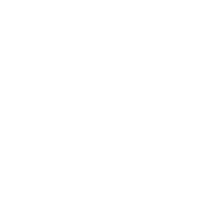李斌奎先生之父100歲生日
(圖:趙社芳)
【和諧中國網(wǎng)·和諧書院】
【編者按】《父親的愛》一文是李斌奎先生寫作于2000年����,當(dāng)時先生的父親八十多歲,如今已是年逾百歲的老人�����。先生少將軍銜�����,著名作家����。1980年,短篇小說《天山深處的大兵》��,獲全國全軍優(yōu)秀短篇小說創(chuàng)作獎,這是新時期軍旅文學(xué)第一個獲獎作品��。隨后����,作者又將其改編成電影《天山行》;其長篇小說巜啊�,昆侖山!》在《當(dāng)代》發(fā)表�����,后由人民文學(xué)出版社出版成單行本�����,遂又改編成電視連續(xù)劇《昆侖山》��,李斌奎的名字�,因此而被載入新時期軍旅文學(xué)史����。

李斌奎先生之父百歲生日慶典上
老父親在蛋糕上親手寫的“100“
(圖:趙社芳)
父親的愛
文◆李斌奎
我的父親是個農(nóng)民,渭北黃土高原上一個最普通的農(nóng)民����。他像所有的父親一樣��,他也像所有的農(nóng)民一樣�����,沒有絲毫的獨特之處����。
從我記事起����,我從來沒有聽見過父親說過愛我之類的話,也不曾見到過父親對我有過任何愛撫��,連拍打一下����、或摸摸我的頭這樣親昵的動作也不曾有過。父親在我的心目中永遠(yuǎn)是嚴(yán)厲的�、忙碌的。每天早早地出門下地�����,回家后總是背著滿身的塵土,之后�����,坐在院子里的臺階上���,脫下鞋�,倒出鞋里的土����,拍打拍打腳,擦把臉說��,吃飯吧�。母親把飯端上來,父親吃的很快��,吃飯時幾乎很少說話�����,飯后照例抽袋煙���。
父親最喜歡抽四川產(chǎn)的葉子煙����,煙葉油黑厚實��,抽時將煙葉剪成一寸長卷在一起�。煙味辛辣嗆人直沖喉管,每當(dāng)此時我總是躲得遠(yuǎn)遠(yuǎn)的��。父親專注地抽自己的煙�����,抽煙是他唯一的愛好�,他顯得很自在安祥,粗糙的臉上每道皺折都很松弛�。他既不會叫我坐在他的身邊,也不會同我談點什么�,似乎我并不存在。抽罷煙后父親又一聲不響地去上工���,時間久了�,我覺得父親離我很遠(yuǎn)很遠(yuǎn)�����。只有母親有時不經(jīng)意地嘆息兩句,日子難過啊��,要不是你爸沒黑沒明地掙工分����,咱家的糧食都分不回來。
李斌奎父李長進老先生百歲華誕慶典
(圖:趙社芳)
遺憾的是�����,那時的我���,對于過日子之類的話并沒有多少感受���。只是發(fā)現(xiàn),漸漸地父親很少抽葉子煙了��。那時一把葉子煙不過四五角錢��,然而����,像父親這樣的壯勞力干一天活生產(chǎn)隊記十分工也不過值七八分錢�����。所以,一把葉子煙父親是買不起的��,偶爾買一把也寶貝似地藏起來�,逢年過節(jié)時抽一支,其余的時間多是抽旱煙�。旱煙是自家的自留地里種的,后來��,農(nóng)民僅有的一點自留地被沒收后����,父親只能在院子里一塊不大的空地上栽幾棵煙苗,常常等不到成熟��,父親便將嫩綠的煙葉摘下來���,在灶火上烤烤揉碎后塞進煙鍋里��。然而���,過了沒多久,父親的這點嗜好也不能維系下去�����,中國人稱作三年自然災(zāi)害的大饑荒到來了。家中不但沒了鹽與點燈的油����,連吃的飯也沒有了,哪還有煙抽�����。為了滿足煙癮���,父親抽棉花葉����、抽樹葉��,每當(dāng)看見他被嗆得咳個不停時��,我隱隱覺出父親的不易����,然而父親浮腫的臉上依然是那樣的堅毅。依然默默地坐在臺階上抽他的“煙”,依然默默地支付著我的學(xué)費�����。至今我都不明白���,家中是怎樣湊齊我的學(xué)費的?我曾經(jīng)問起過父親���,可父親只是說����,再難也得讓你上學(xué)?��?��!因為我是家中的獨子!母親隨之傷感了����,她擦著眼淚說,我娃上學(xué)那陣子把罪受了�,連飯都吃不上。我就再也不能提這類的話題了。
確實����,在那大饑荒的年月里,我真正懂得了饑餓是什么樣 ��!
當(dāng)時���,我正是讀完中學(xué)升入高中的時候���,由于饑餓,學(xué)校的體育課停了���,連早操也不再出����,但是�����,同學(xué)們和老師還是無力支撐每天的幾個課時�,浮腫像瘟疫一樣漫延開來。不少同學(xué)輟學(xué)離去����,有些家在外地的老師把全部的工資買成黃豆�,炒熟后裝在衣袋里����, 上課時支持不住了摸出兩粒填在嘴里��,一邊嚼一邊講課���。那時一粒黃豆就像一粒金豆子那樣珍貴��。我們眼瞅著老師蠕動的嘴直咽口水�,心里只有一個念頭——直盼著快點下課�, 到哪兒能找點吃的。當(dāng)下課鈴響起時�,我們就像一群饑民不顧一切地往家奔。
從學(xué)校到我家不過一百多米遠(yuǎn)��,出了校門一條大路�����。這是一條我走了不知多少次的路����,可那時我覺得那條路是那樣長��,像是比跋山涉水還要艱難��。走兩步就氣喘吁吁��,眼前一片黑��,我不得不坐下來喘口氣�。就這樣走走停停����,停停走走,一百米的路我休息了四五次才挨到家��。進了家門�����,我一屁股坐下來再也起不來了�。我對母親說,我病了���。母親說�����,你哪是病了����,你是餓了。掀開鍋�����,鍋內(nèi)留下一碗糊糊�����。名為糊糊�,實際清清的湯水都能照見人影�����,這就是我全部的食物���。我一口氣喝下去����,又把碗舔干凈。我問母親還有嗎�?母親背過身去。我后悔自已不該太不懂事�����,因為這碗稀湯還是母親和父親餓著肚子省下來的���。
饑餓是難耐的��,無論我如何理解家中的艱難�����,但每到夜里還是睡不著覺�����,肚子里像著了荒火����。好不容易閉上眼睛�,忽然聽到窯洞門被打開了,一陣呼呼的喘氣聲把我驚醒��。我爬起來,看見父親背著一口袋東西走進來����。他滿頭的汗水,進門后人同口袋一起蹲在地上��,有氣無力地說���,有什么吃的嘛���,我實在撐不住了。母親從炕洞里取出了一個煨熟的蘿卜�����,父親連外面的炕灰也沒有彈���,就連皮一起吞下去。又喝了幾大碗水����,才長長地吁出一口氣。
原來�,家里已經(jīng)斷糧幾天了�����,父親走了一趟武帝山����,托山下的朋友買了點黑豆�。在那時,一切有關(guān)糧食的買賣都被視為非法��,哪怕是普通百姓為了活命����。所以,父親趁夜走了四十多里山路偷著趕去�����,又連夜趕回來�。往返八九十里地,父親又餓著肚子��,真不知道他是如何把這袋糧食弄回家的�。母親要父親快上炕歇歇,父親擺擺手說��,別歇啦 ,眼看天就要亮了���,趕快把這糧食收拾一下�����,天亮了�����,孩子就得吃飯���,吃完飯還要上學(xué)呢!父親隨即打開了口袋���,這才發(fā)現(xiàn)黑心的朋友竟在糧食中塞了兩塊磚��。父親的手抖開了!我永遠(yuǎn)也忘不了父親那張被悲愴與憤怒扭曲了的臉�����。
母親常愛說一句話——出一天太陽吃三頓飯�,年好過����、節(jié)好過���、日子難過���。我嫌母親嘮叨。然而���,饑餓使我明白了媽媽這句話的含意��。我的家是個大家庭����,我雖然是個獨子�,可家中還有奶奶爺爺,叔父一家也與我們同住一院��。很快����,父親弄回來的一點黑豆又吃光了,家里又陷入了窘境。父親常?�?粗炜?��,而太陽已不再是什么神圣的圖騰了�,它既不鮮艷�,也不明亮,整日價都是暗黃色的��、并有些混濁����,它老掛在天上,把煎熬懸在人們的頭頂�。父親問母親,現(xiàn)在的白天怎么那么長�?母親說,災(zāi)年的白天都這樣��,民國十八年的白天就特別長�����。
民國十八年陜西遭受了大饑荒���,這次饑荒對于一貫活得比較平隱的陜西人來說留下永遠(yuǎn)抹不掉的記憶���。不過,父親說��,民國十八年雖然遭了饑荒�,可街道上賣什么吃的都有,糧食也是隨處可以買到的�����,只是�����,許多的人沒有錢罷了��。而這次饑荒卻是徹徹底底的饑荒�,無形的桎梏把無望的人們死死地釘死在饑餓線上,而不甘于坐以待斃的人們只有自己尋找生路了���。
白天����,父親等待著飼養(yǎng)員老王的吆喝聲,他的聲音意味著生產(chǎn)隊又一頭牲畜餓死了��,這樣父親就能提回一點血淋淋的牛肉或馬肉�����;到了夜晚��,幾乎所有的莊稼人都出門去尋找一切可能得到的食物�。父親也不例外。從地里回來常常是深夜����,母親一直在擔(dān)心,父親對母親說����,用不著擔(dān)心,人們都餓瘋了����,地里滿山遍野都是人,像是趕集一樣�����。
 作家李斌奎先生(中)
作家李斌奎先生(中)
就在這年秋天的一個夜晚,父親出門后沒多久�����,天下起了小雨���,不大功夫,雨越下越大����,家里窯洞背上的水嘩嘩地往下淌,發(fā)出了震耳的響聲��。積水流淌的聲響在夜風(fēng)里格外的嚇人�。母親像是有什么預(yù)感,她不時地打開窯洞門����,跑進黑沉沉的雨地里。半夜時分��,父親被同去的鄰居背了回來���,他滿身的泥水���,臉色蒼白�,時斷時續(xù)地發(fā)出呻吟聲��。同去的鄰居告訴母親�,因為雨大風(fēng)大,什么也看不清楚��,父親失腳跌到幾丈高的土崖下��。多虧被雨水泡過的地松軟些��,否則父親就沒了命�!
母親哭了,我也走到父親的身邊��。父親拉住了我的手����,父親粗硬的大手又冰又冷,也許平日里沒有此種的交流����,我本能地想把手縮回去,可父親硬是拉住不肯放松�。他勉強從臉上擠出一點苦笑�,抽動著嘴唇說���,沒事����,你快點睡覺去��,明天還要上學(xué)去呢��!不知為什么�,我的心像是突然被人攥了一把����,眼淚不知不覺地流了下來。
我明白���,父親不顧一切的搏命都是為了我的學(xué)業(yè)���,他不止一次地說過,你的母親多病�,他希望我成為一個醫(yī)生。這是父親的一個夢�,一個唯一依附在兒子身上的夢��。也許�,正是這個夢使父親奇跡般地拖著全家人渡過了三年的饑荒����,可是,文化大革命卻使父親的夢想徹底破滅了�����。當(dāng)武斗的槍聲響起時����,幾乎每天都有人朝著我家的方向打槍,為了保護我這個唯一的兒子���,父親斷然將我關(guān)在家中����,不許我出門����。這是父親第二次限制我的行動,第一次是我上初中時,縣劇團來學(xué)校招生�����,父親怕我報名將我關(guān)起來�����?���?墒牵涠吩絹碓郊ち?��,當(dāng)形同匪幫的槍手們隨意殺人時,在一個暮色蒼茫的黃昏��,冒著急飛的彈雨�,父親搭起梯子,將我扶上窯背�,翻墻跳到隔壁,越過金水溝把我送到了鄉(xiāng)下舅舅家���。為了讓我安心住下��,父親留下我平時愛讀的小說��、還掏出了一包“紅金”牌香煙塞給我��。我楞了����。那時我并不怎么抽煙,只是因為好奇�,偷著抽一支。沒想到父親已經(jīng)知道了����,還買來好煙給我抽。正是從那時起我覺得自己是個男人���。父親用無言的行動使我意識到自己已經(jīng)長大了����。于是�����,在無可選擇的年代�����,我選擇了唯一可行的路——當(dāng)兵!我唯一的理由是���,我既然已經(jīng)長大了��,就必須找到一碗飯吃��,才能養(yǎng)活父母�����,養(yǎng)活這個家呀����!一個獨生子去當(dāng)兵����,我以為父親無論如何是不能同意的����,但是,父親用沉默����、母親用淚水送走了我����。
 陜西合陽中學(xué)馬緒民校長看望李斌奎先生
陜西合陽中學(xué)馬緒民校長看望李斌奎先生
從此��,我別離了父親����。當(dāng)再次見到父親時,已是三年之后���。到家之際����,我才知道�,父親收到我要探家的信后,幾乎每天都要去車站等候�,他幾乎等了十多天,雖然別人告訴他我半個月后才能回來�����,可他照樣一大早就去了車站��,直到最后一趟班車上的人全部走散才失望地走回來。老漢想兒子想瘋了���!鄰居們不無感嘆地對我說起此事����,打那之后���,我再也不敢提前寫信�,告訴我探家的事��?��?筛赣H像是有預(yù)感��,又像是算計過了���,每到我即將探家的時候,他就照樣去車站等候��,可也怪��,多少年來�,沒有一次父親能接上我。每次����,當(dāng)我意外地出現(xiàn)在父母親面前時,父親只是問問���,你坐哪趟車�����,然后便一直坐下來抽煙����,再也沒了話語�����,一點也看不出興奮和激動的樣子�。只是有一年,我去了海拔5000多米的邊防哨所�,由于嚴(yán)重的高寒缺氧,導(dǎo)致我胃部大出血��,治療了一段抱病回家時����,父親得知時急不可待地對我說���,趕快到醫(yī)院走,爸給你輸血��!那年父親已是六十五歲了����!
就這樣,在家住了一個多月�,等身體稍稍復(fù)原,我又要歸隊了�。像往常那樣,父親一定要提著行李親自送我去車站���;母親站在門外��,當(dāng)我走出幾步再回頭時�����,發(fā)現(xiàn)父母親的頭發(fā)在不知不覺中已經(jīng)白了�����,心內(nèi)由不得一陣酸楚�。而父親并沒有多余的話�,連愛護身體之類的語言也很少說,只是默默地望著車子遠(yuǎn)去���。就這樣一年又一年的送別���,直到今年,父親患了感冒��,半個多月也過不去�,而我又要走了。這回�,父親沒了往年的沉默,就在我出門時��,父親眼圈突然紅了����,接著止不住地抽泣起來。這是我第一次看見父親流淚��,哪怕在最困難的年月里���,父親從來沒有當(dāng)著我的面掉過淚����。
父親老了,他已經(jīng)八十多歲了��,再也克制不住對兒子的思念�����,他多想我一直陪伴在他的身邊�����,這是他唯一的要求?��?����!當(dāng)時我只是在心里默默地對著上蒼說��,我是個軍人�����,我還得走?�?��!但愿我的父親永遠(yuǎn)健康長命百歲!
2000年于蘭州
 李斌奎先生(前排中)2011年出席
李斌奎先生(前排中)2011年出席
陜西合陽縣首屆《弟子規(guī)》誦讀大賽
(圖:李宏)
 李斌奎先生(前右五)在
陜西合陽縣首屆《弟子規(guī)》誦讀大賽上
李斌奎先生(前右五)在
陜西合陽縣首屆《弟子規(guī)》誦讀大賽上

陜西合陽縣公安局”文化名家進警營“之
李斌奎先生談文藝創(chuàng)作

李斌奎先生在陜西合陽供水公司授課
【投稿】和諧中國網(wǎng)
郵箱:731590068@QQ.com
微信:131 4145 7599